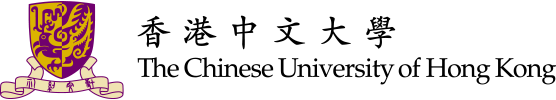| 第89届大会 (2020)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荣誉理学博士 |
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于1966年生于现称Chennai市的印度Madras市。翌年,他父母携他远渡重洋到英国,在Cheshire市内的Runcorn镇边陲定居,此镇现已纳入利物浦市,教授的童年就在此区度过,相信很多人会因此羡慕他。1967年,利物浦市平地一声雷,凭藉市内出色的摇摆乐队,迅速爆红,疯魔全球。而披头四乐队在此推出其最具代表性的唱片专辑: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内有两首划时代的歌曲,其中一首是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此曲脱胎自Lewis Carroll的Alice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提起Carroll这名字,很多人就联想到牛津,但Carroll的出生地并非牛津,而是Daresbury这教牧区,与Daresbury小学相隔只是数步之遥。Balasubramanian教授启蒙于这所小学,而他和家人在这充满创意的环境下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其后,教授转往Appleton Hall中学升学,继而于1985至1988年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学院(Fitzwilliam College)修读自然科学,考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现在回想,这初期的成就已清楚显示教授的学术潜力。毕业后教授继续在剑桥深造,追随Chris Abell教授钻研酶(又称酵素)化学(Enzymes Chemistry),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事业轨道上迈出重要一步。酶是可对各种化学反应产生催化作用的生物分子,撮合及加速分子与分子之间的化学反应(但过程中其质与量丝毫无损,历久不衰 ……)。
在日常生活中,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身体由细胞构成,而个别细胞内的新陈代谢反应都有酶的影子,否则,所有这些反应皆会因为速度太慢而不能维系生命。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若有一种酶能将平常需时数以百万年计的发酵过程缩短为千分之一秒,这种酶定必成为制药的良方 — 不论良药或毒药。氰化物(俗称山埃)当与名为C细胞色素的酶起作用,可堵塞细胞内的主要氧代谢通道,即能在瞬息间致人于死地。幸而我们的荣誉博士领受人绝不是一位施毒者,他的酶研究工作初衷是将成果惠泽众生。他从研究中找出钥匙开启我们的遗传密码,不单是你的或是我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体内的不同基因表达(expressions of genes)。教授是如何达致这研究目标的?
在1991年,Balasubramanian博士离开剑桥,由东往西横渡大西洋,跟随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Stephen Benkovic教授做博士后的研究,为时两年,这亦是教授生平仅有的一次离开剑桥。教授紧随四分一世纪前Harvey Lodish教授的轨迹,继续酶的研究工作,并和Benkovic教授合作,共同出版了数篇学术文章,集中研究由人类免疫缺乏病毒(HIV)抽取出来的一种酶,文章发表后得到其他学者广泛的引述。可是,宾夕法尼亚虽具魅力,剑桥毫无疑问更具吸引力(说真的,剑桥的吸引力有时在牛津也感受得到)。当时英国皇家学会开始提供研究奖学金,让英国大学设立研究员席位,招聘崭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进行独立创新的科研项目,这无疑是条光明大道。为此,1994年再见Balasubramanian教授回归剑桥,亦是他最后的一次,自此教授长居此地。
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神秘结构是在剑桥解开的。这个发现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开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新境界。可是要令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甚至只是一窥,更遑论要去塑造这些可能性,我们都必须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读这些DNA中蕴藏的遗传密码,继而寻找操控它们的方法。在剑桥,Fredrick Sanger教授在这领域踏出关键性的第一步,他找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去解读甚或列序DNA。Sanger教授的方法使他第二次获颁诺贝尔奖,是项发明亦令「人类基因组计划」(The Human Genome Project)得以进行。这项划时代研究项目始于1990年,历时十三年多,耗资三十亿美元以上,其目标是于2003年至少完成DNA测序工作的初步报告。但是,当这个庞大的国际性科研项目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在剑桥,相关的研究工作已为该项目打下基础,把相若的科研项目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速度。Balasubramanian教授在返回剑桥后,在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作研究员,与牛顿隔代辉映。他与David Klenerman教授共同研究DNA聚合酶(DNA polymerase)。聚合酶乃一种可促成产生生物聚合物的酵素,令人体内较细小的同类分子聚合成为一群庞大的生物分子。凭藉这研究工作,他们发现将DNA结构列序的新方法,日后并将此方法应用到普及层面。
摩尔定律(Moore’s Law)预言电算机运算能力每十八个月便会倍增,但教授新DNA列序方法所产生的变化更巨大。DNA的列序工作,不久前仍需依赖庞大和持续的国际项目,然而,藉着教授的新方法,现只需少于原来的百万分之一的成本,而且速度快一百万倍。电算机运算能力的提升当然是原因之一,但若没有教授的新方法,我们可能需要更长日子,才能成就列序DNA这艰钜任务。Balasubramanian教授所研发的新方法,对此项研究至为重要。
Dominus illuminatio mea ,意思是「救主是我光」(The Lord is my light),是牛津大学创校以来的校训。但在今天,很多科学家和临牀医生都可能说Illumina dominus meus (Illumina是我主),因为以Illumina为名的一所科研公司,采用Balasubramanian 教授和Klenerman教授的科研成果为核心技术,为客户提供新DNA序列方法,不单准绳度高,且快捷可靠,而更重要的是收费大众化。如这技术不存在,大多数现代的产前诊断检测或癌症诊断均不可行。教授的研究成果对科技和病人福祉实乃一大贡献。至此,或许你认为我将用一两句说话,作为此赞辞的终结,以表扬教授的贡献。不对,我还有话说。
我们的基因全在我们的DNA内,基因把我们塑造成「人」,并决定我们可传承甚么给下一代。然而人体不同部位的组织是不一样的,如皮肤、肝、牙齿、肠道、味蕾、头发和大脑:所有这些不同的组织,皆由相同的DNA所控制;这是因为人体内的基本基因,在这些组织的生长过程中,能按着特定调控机制,不断打开及关闭。这些高阶的调控机制,亦受人体遇到的不同境况所影响,包括环境因素或药物作用等;基因开关造成的改变,以及受影响的基因,一部分都会传承给下一代,以至代代相传,影响我们儿孙的个别基因表达。上述的过程就是所谓「表观遗传变化」(epigenetic changes),这现象亦为遗传学开创了新的学章。这些表观遗传变化,并不出现在基因本身,而是指基因可以造成影响的能力,就如不断就DNA发出的讯息作出旁白一样。维根斯坦曾有此一问:「若狮子能说话,我们可会听懂它的话?」(最佳答案当然是「不」)。除非我们了解表观遗传学及遗传学,否则我们不会明白蕴藏在DNA内的密码。为此,你会明白为什么Balasubramanian教授并不对他在传统DNA列序的研究成果自满,而是再接再厉地把他的研究方向聚焦于「表观遗传列序」(epigenetic sequencing)。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对教授的研究说个大概,但应已足够让你们听到2012年教授已为表观遗传列序这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感到惊讶,同时亦对教授的研究能力深感佩服。他的研究成果,亦藉一所公司转化为社群服务,让基本生物学家及临牀医生受惠。能开花结果的创意构想,必然是最有价值的构想,而教授的表观遗传列序研究是其中表表者,亦为个人化诊治带来美好的愿景,及随之而来的众多好处。
Balasubramanian教授所获荣誉与嘉许无数,今天的荣誉博士名衔只是教授众多荣耀之一,大学与有荣焉。本人谨恭请主席阁下颁授荣誉理学博士衔予Shankar Balasubramanian爵士,「一位利用萤光照亮人类传承的智者」。